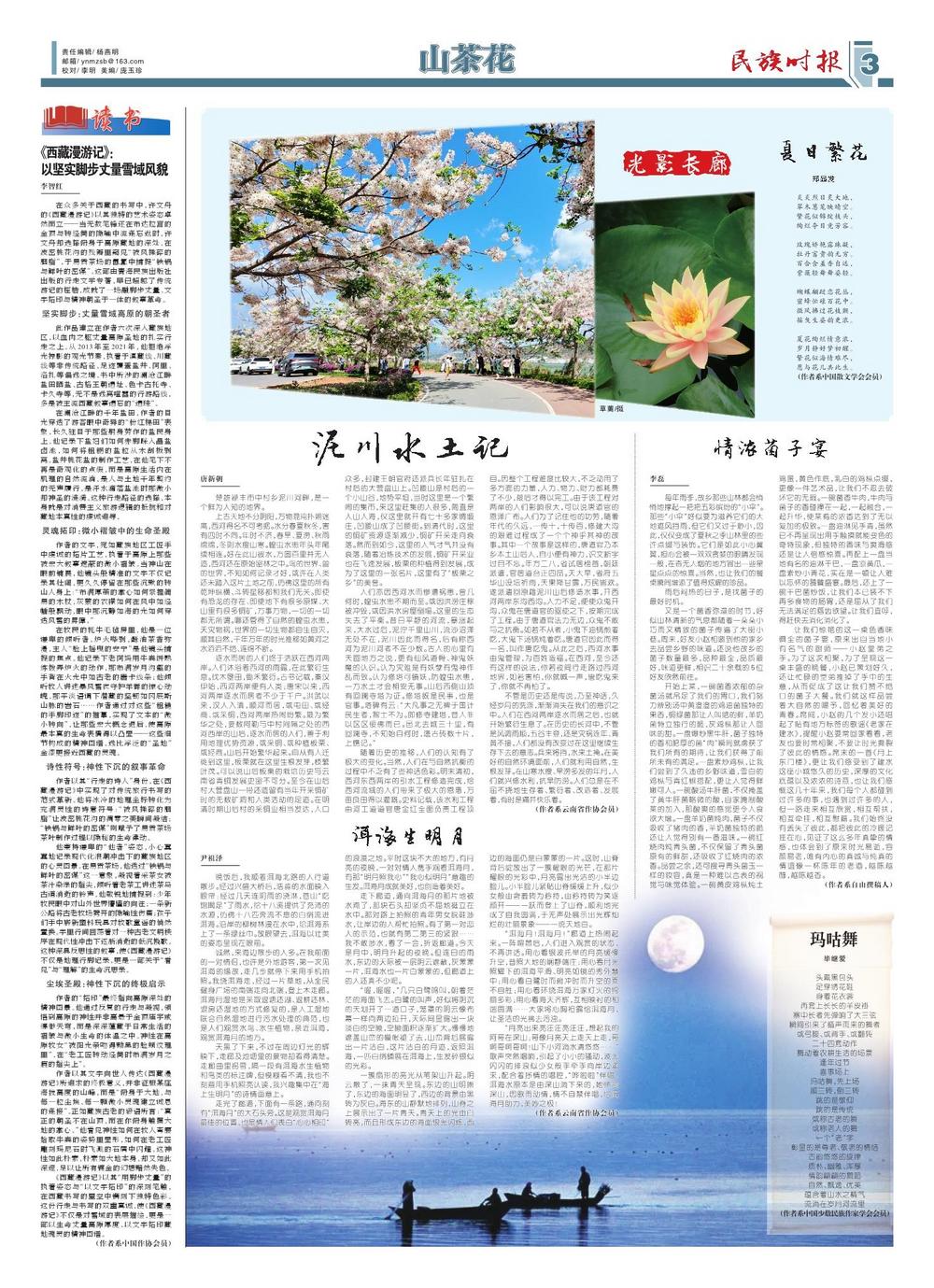唐新朝
楚雄禄丰市中村乡泥川河畔,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界。
上古天地不分阴阳,万物混沌扑朔迷离,西河得名不可考据。水分春夏秋冬,害有四时不同。年时不济,春旱、夏涝、秋雨绵绵,冬则水瘦山寒。蝗虫水患年头年尾续相连。好在此山彼水,方圆百里并无人迹,西河还在原始密林之中。鸟的世界、兽的世界,不知如何记录才好,或许在人类还未踏入这片土地之前,仿佛这里的所有乾坤纵横、斗转星移都和我们无关。即使有恐龙的存在、即使地下有很多原煤、大山里有很多铜矿,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无所谓。哪还管得了自然的蝗虫水患,天灾物祸,世界的一切生物都自生自灭,顺其自然,千年万年的时光推移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
逐水而居的人们终于活跃在西河两岸。人们沐浴着西河的雨露,在此繁衍生息。伐木垦田,锄禾繁衍。古书记载,秦汉伊始,西河两岸便有人类;唐宋以来,西河两岸逐水而居者不少于千户。洪武以来,汉人入滇,顺河而居,或屯田、或经商、或采铜,西河两岸热闹纷繁。最为繁华之处,要数阿勒与中村间隔之处的西河西岸的山后,逐水而居的人们,善于利用地理优势资源,或采铜、或种植板栗、或经商。山后开始繁华起来。自从有人迁徙到这里,板栗就在这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可以说山后板栗的栽培历史与云南省青铜发展史密不可分。至今在山后村大营盘山一带还遗留有当年开采铜矿时的无数矿洞和人类活动的足迹。在明清时期山后村的采铜业相当发达,人口众多,封建王朝官府还派兵长年驻扎在村后的大营盘山上。凹腰山是村后的一个小山谷,地势平坦,当时这里是一个繁闹的集市,来这里赶集的人很多,简直是人山人海,仅这里就开有七十多家绸缎庄,凹腰山成了凹腰街。到清代时,这里的铜矿资源逐渐减少,铜矿开采走向衰落。然而到如今,这里的人气才气并没有衰落,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铜矿开采业也在飞速发展,板栗的种植得到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张名片,这里有了“板栗之乡”的美誉。
人们亦因西河水而惨遭祸患,曾几何时,蝗虫水患不期而至。或因洪涝庄稼被冲毁,或因洪水房屋倒塌。这里的生态失去了平衡。昔日平静的河流,暴涨起来,大水过后,泥泞千里山川,流沙沼泽无处不在,泥川因此而得名,后有称西河为泥川河者不在少数。古人的心里有天圆地方之说,更有仙风道骨、神鬼妖魔的认识。认为灾难是有妖孽有鬼神作乱而致。认为修塔可镇妖,防蝗虫水患,一方水土才会相安无事。山后西侧山顶有回澜寺塔为证。修塔既是民事,也是官事。塔碑有云:“大凡事之无禆于国计民生者,智士不为。即修寺建塔,昔人非以区区佞佛而已。邑北去城三十里,有回澜寺,不知始自何时,遗古砖数十片,上镌记。”
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的认知有了极大的变化。当然,人们在与自然抗衡的过程中不乏有了些神话色彩。明末清初,西河东西两岸的引水工程修造完成,给西河流域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恩惠,万亩良田得以灌溉。史料记载,该水利工程由河工道道官唐金红全面负责工程项目。因整个工程难度比较大,不乏动用了多方面的力量,人力、物力、财力都耗费了不少,最后才得以完工。由于该工程对两岸的人们影响很大,可以说唐道官的恩泽广布。人们为了记住他的功劳,随着年代的久远,一传十,十传百,修建大沟的艰难过程成了一个个神乎其神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唐道官乃本乡本土山后人,自小便有神力,识文断字过目不忘。年方二八,省试居榜首,朝廷派遣,官居道台正四品。天大旱,省府五华山设坛祈雨,天果降甘露,万民皆欢。遂派遣回原籍泥川山后修造水事,开西河两岸东沟西沟。人力不足,便使众鬼开沟,众鬼在唐道官的驱使之下,按期完成了工程。由于唐道官法力无边,众鬼不敢与之抗衡。如若不从者,小鬼下油锅煎着吃,大鬼下汤锅炖着吃。唐道官因此而得一名,叫作唐吃鬼。从此之后,西河水事由鬼管理,为百姓造福。在西河,至今还有这样的说法,你若夜间行走路过西河地界,如若害怕,你就喊一声,唐吃鬼来了,你就不再怕了。
不管是历史还是传说,乃至神话,久经岁月的洗涤,渐渐消失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人们在西河两岸逐水而居之后,也就开始繁衍生息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管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是灾祸连年、青黄不接,人们都没有改变过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意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美好的自然环境面前,人们就利用自然,生根发芽。在山寒水瘦、旱涝多发的年月,人们就兴修水利,抗旱防涝。人们总是在不屈不挠地生存着、繁衍着、改造着、发展着,有时是痛并快乐着。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